1900年的北京,入秋就冷得早,胡同里的槐树叶子落了一地,扫街的老张头裹紧了棉袄,却没像往常一样吆喝,只蹲在墙角,盯着地上的白灰圈叹气。那圈里是隔壁李家的小儿子,前几天还追着他要糖吃,这会已经烧得迷迷糊糊,脸上起满了红疹子——是天花,老北京人最怕的“痘症”。
那时候,遇上天花,老百姓要么求神拜佛,要么找“痘师”来“种痘”。所谓种痘,是把得过天花的人身上的痘浆,挑一点出来,在健康人胳膊上划个小口,让他轻微染病,盼着能扛过去。可这法子太险,十个人里总有两三个扛不住,反而送了命。李家就是怕这个,犹豫了两天,孩子的疹子已经冒白尖,痘师来了也摇头:“晚了,这痘发透了,只能听天由命。”
老张头看着李家媳妇哭天抢地,心里也发紧。他想起二十年前,自己的小女儿就是这么没的,那时候他也请了痘师,可痘浆刚种上,女儿就烧得直抽风,没撑过三天。那时候他就想,这世上就没个能安安稳稳防天花的法子吗?
还真有。这年冬天,通州的教堂里来了个英国医生,叫梅藤更,背着个黑皮箱子,里面装着小玻璃瓶,说是能“防痘”,不用挑痘浆,只用针管打一点“药”就行。消息传出来,老百姓都躲着走,说这是“洋鬼子的邪术”,打了会让人变“洋鬼子”。有个乡绅还带着人去教堂门口闹,说“咱们老祖宗的痘法用了几百年,哪用得着洋人的东西”。
梅藤更没急着辩解,只是在教堂门口摆了张桌子,每天给路过的人讲天花的厉害,还拿了两张图——一张是得过天花的人,脸上坑坑洼洼;一张是种过“洋痘”的人,皮肤光滑。有人好奇,问他“这药到底是啥?”梅藤更说:“是从牛身上取的痘浆,比人痘温和,种了之后顶多胳膊肿两天,不会送命。”
还是没人敢试。直到有天,一个叫王二的脚夫跑来找他。王二的媳妇刚生了娃,听说天花专找小孩,他急得睡不着觉,心想“反正老法子也危险,不如试试洋的”。梅藤更当场给王二的娃种了痘,只用针在胳膊上扎了一下,挤了点乳白色的药进去。过了几天,王二抱着娃来谢他,说娃除了胳膊肿了点,啥事儿没有,连发烧都没烧。
这事儿一传开,来种痘的人慢慢多了起来。梅藤更还教当地的中医配药,说种痘后要是发烧,喝几副清热的药就行。后来,官府也听说了,觉得这法子能少死人,就让梅藤更去各个县城推广。有个县令一开始还不乐意,说“洋人的东西进了我的地盘,老百姓该说我崇洋了”,可看着邻县种痘的地方,天花死的人比自己这少一半,也赶紧派人去请梅藤更。
这“洋痘”,就是后来咱们说的牛痘疫苗。它比人痘安全,效果还好,慢慢从通州传到北京,又传到天津、上海。到了1910年,全国已经有十几个城市能种牛痘,虽然还是有老百姓不信,但至少多了个能躲天花的法子。可谁也没想到,这年冬天,另一种更凶险的传染病,又从东北冒了出来——鼠疫。
1910年10月,黑龙江的满洲里,一个俄国人开的煤矿里,有两个矿工突然发烧、咳嗽,痰里带血,没两天就死了。一开始没人当回事,以为是普通的风寒,可没几天,矿上又死了十几个人,症状都一样。矿主怕影响生意,偷偷把尸体埋了,可还是没挡住——鼠疫像长了腿,顺着中东铁路,往哈尔滨跑。
到了11月,哈尔滨的傅家甸已经乱成了一锅粥。街上的铺子关了大半,家家户户都插着柳条,说是能“驱邪”。有个药铺老板趁机卖“避瘟散”,几文钱一包的草药,炒到了一两银子,可买的人还是挤破头。更吓人的是,有些人家早上还好好的,晚上就全家病倒,第二天门就锁了,里面悄无声息——要么是都死了,要么是被邻居抬去乱葬岗了。
官府也慌了神。哈尔滨道台想派兵把傅家甸围起来,可士兵们听说里面有鼠疫,没人敢往前冲,有的还偷偷跑了。这时候,有人想起了伍连德——一个在英国学过医的中国人,刚在天津办了医学院,懂传染病。清廷赶紧发电报,让伍连德去哈尔滨,不管用啥法子,先把鼠疫按住。
伍连德到哈尔滨的时候,傅家甸的积雪已经没了脚踝,空气里都飘着一股消毒水的味道。他没先去官府,直接去了乱葬岗,扒开积雪,看了几具尸体——死者的肺部都烂了,嘴里还留着血。他又去看了几个病人,发现他们大多是矿工、铁路工人,都是住得挤、来往频繁的人。伍连德心里有了数:这鼠疫不是通过老鼠跳蚤传的,是通过飞沫传的,跟感冒一样,说话、咳嗽都能传染。
要防飞沫,就得戴口罩。伍连德找了家工厂,让工人用纱布和棉花做口罩——两层纱布中间夹一层棉花,绑在脸上,能挡住唾沫。他把这口罩叫“伍氏口罩”,让官府免费发给老百姓,还派人在街上教大家怎么戴。可一开始没人愿意戴,说“捂着嘴喘不过气”,还有人说“戴了就是承认自己有病”。伍连德没办法,只能带着医生和官员先戴,走在街上给老百姓示范:“你看,戴了这个,就不会把病传给家人了。”慢慢的,戴口罩的人才多了起来。
光戴口罩还不够,得把病人隔离开。伍连德找道台要了几间空房子,改成“隔离医院”,把病人分着放——轻的放一间,重的放一间,接触过病人的人也单独关起来,不许出门。可老百姓哪肯去隔离医院,说那是“关大牢”,有家人被带走,还哭闹着要去抢人。伍连德只能让士兵在隔离医院门口守着,又找了当地的乡绅,让他们去劝老百姓:“隔离不是害你们,是救你们,要是一家人都染了病,谁来照顾孩子?”
最难的是处理尸体。那时候哈尔滨已经死了几千人,尸体堆在乱葬岗,有的冻在雪地里,有的已经开始腐烂,鼠疫菌在尸体里繁殖,越堆越危险。伍连德想把尸体烧了,可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——中国人讲究“入土为安”,烧尸体是对死者的不敬。道台不敢拍板,说“这事儿得朝廷同意”。伍连德赶紧给北京发电报,说“不烧尸体,鼠疫永远好不了”。清廷犹豫了三天,最后还是同意了。
烧尸体那天,傅家甸的老百姓都站在远处看。几十具尸体被抬到空地上,浇上煤油,一把火点着,火光映红了半边天。有人哭,有人骂,可看着火越烧越旺,也没人敢上前。烧完之后,伍连德又让人把乱葬岗的雪挖开,撒上石灰,彻底消毒。
就这么着,戴口罩、隔离、烧尸体,三个法子一起用,到了1911年3月,哈尔滨的鼠疫终于控制住了——每天新增的病人从几百个降到了零。伍连德又把这法子推广到东北其他地方,没几个月,整个东北的鼠疫都平息了。这是中国第一次用科学的法子防治大规模传染病,伍连德也成了老百姓眼里的“救命大夫”,有人还给他立了长生牌,说“是伍大夫救了咱们东北人”。
鼠疫刚过,大家又想起了天花。这时候,牛痘疫苗已经比以前方便多了——以前得用玻璃瓶装,靠冰块保温,运到偏远地方就坏了;现在有了“冻干疫苗”,用锡管装着,不用冷藏,能运到乡下。民国政府还专门成立了“防疫处”,让医生背着疫苗,走村串户去种痘。
有个叫丁福保的医生,在江苏推广种痘的时候,遇到过一个固执的老太太。老太太说“我孙子不种痘,我当年就是种痘差点死了”。丁福保没跟她争,只是把自己胳膊上的种痘疤痕给她看:“您看,我这就是种的洋痘,几十年了,啥事儿没有。您孙子要是种了,以后就不怕天花了。”老太太还是不信,直到邻居家的孩子种了痘,后来村里闹天花,那孩子真的没事,她才抱着孙子来找丁福保:“大夫,您快给我孙子种痘,我以前是老糊涂了。”
到了1929年,全国大部分城市都能免费种牛痘,农村也有流动的种痘队。那时候,街上已经很少能看到脸上有天花疤痕的人了。有人问丁福保:“这牛痘能把天花赶跑吗?”丁福保说:“只要人人都种痘,总有一天,天花就再也不敢来了。”
他这话还真说对了。新中国成立后,政府更是把种牛痘当成大事,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,都组织大家种痘,连偏远的山区都没落下。1961年,中国最后一个天花病人在云南被治好,从那以后,中国就再也没有过天花病例。1980年,世界卫生组织宣布,全球消灭天花——这其中,有中国几十年推广牛痘疫苗的功劳。
回头看这几十年的传染病防治,不管是天花还是鼠疫,最管用的法子其实就两个:一个是接种疫苗,从源头防住;一个是隔离病人,切断传播。这法子看着简单,可在当年,要推行开来,比打仗还难——得跟旧观念斗,跟恐慌斗,还得跟有限的条件斗。可就是凭着医生们的坚持,官府的支持,还有老百姓慢慢的理解,这些法子才扎下了根,救了无数人的命。
就像1900年北京胡同里的老张头,他没等到天花被消灭的那天,可他要是知道,后来的孩子不用再怕天花,不用再受种人痘的罪,肯定会笑着说:“当年那洋大夫的法子,还真管用。”而1911年哈尔滨的老百姓,要是知道他们经历的鼠疫防治,后来成了中国防疫的样板,遇到传染病的时候,大家都会戴口罩、搞隔离,也会觉得,当年那场辛苦没白费。
传染病从来没离开过人类,可人类也从来没怕过。从牛痘疫苗到伍氏口罩,从隔离医院到全民防疫,每一次防治传染病的斗争,都是一次经验的积累,一次观念的进步。现在我们遇到传染病,知道要打疫苗、戴口罩、少聚集,这些习惯,其实都是从当年那些故事里来的——是无数医生、官员、老百姓一起,用汗水和智慧,给我们留下的“防疫规矩”。
这些规矩,没什么惊天动地的,可就是靠着这些规矩,我们一次次挡住了传染病的进攻,保护了自己和家人。就像当年伍连德在哈尔滨说的:“防疫不是一个人的事,是所有人的事。只要大家都守规矩,再厉害的传染病,也能打败。”这话,到现在还管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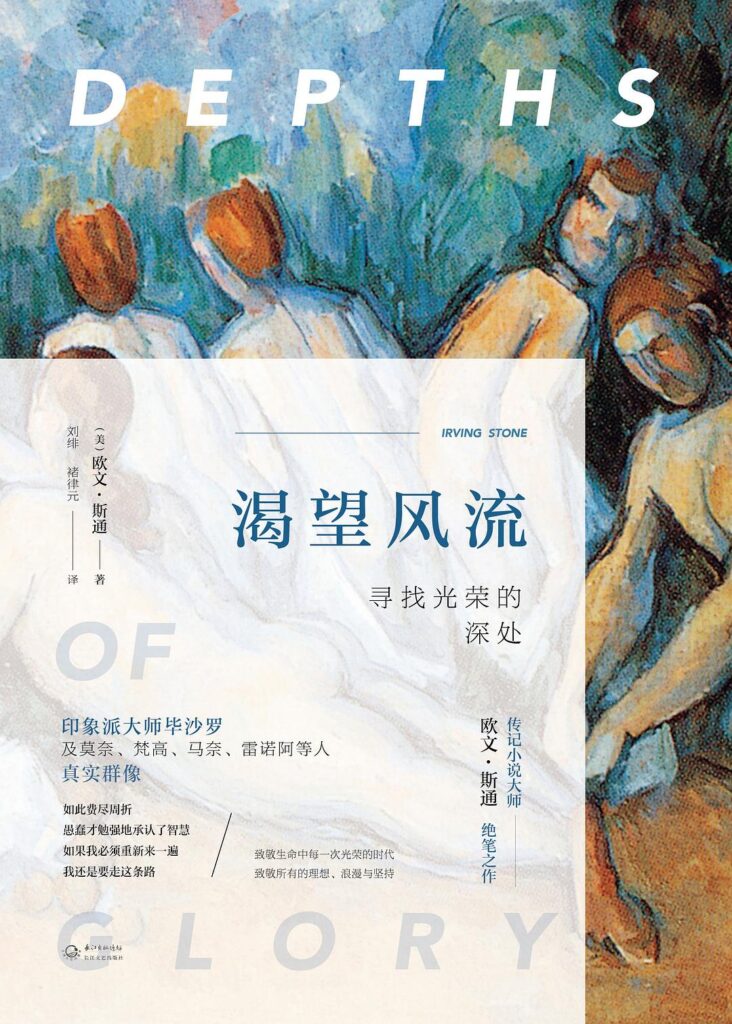




近代传染病防治:接种疫苗、隔离病人应对鼠疫、天花:等您坐沙发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