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05 年的上海,初夏的太阳已经有点晒人。十六铺码头的栈桥上,陈阿福扛着半人高的粮包,一步一挪地往船上送。肩膀上的粗布垫早就被汗水浸透,磨得皮肤又红又肿,稍微一动就疼得钻心。他才十七岁,从江苏乡下逃荒来上海,没读过书,除了卖力气啥也不会 —— 码头的活干一天算一天,遇到雨天没活干,就得饿肚子。
这天傍晚,陈阿福蹲在码头边啃干馒头,看见几个穿短褂的人围着一张红纸看,还时不时点头议论。他凑过去,听一个戴眼镜的先生念:“江南制造局招工,办技工学校,学铁匠、木匠、机修,管吃管住,毕业还能留局里当技工。” 陈阿福愣了愣,“技工学校” 是啥他不懂,但 “学手艺”“管吃管住”“当技工” 这几个词,像钩子一样勾住了他 —— 要是能学个手艺,总比天天扛包强吧?
他攥着手里的干馒头,犹豫了半天,还是跟着那几个人去了江南制造局。门口的差役看他穿得破破烂烂,皱着眉想赶他走,幸好戴眼镜的先生拦了下来:“只要愿意学,不管出身,都能来试试。” 就这样,陈阿福成了江南制造局技工学校的第一批学生。他不知道,自己赶上的,是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的头一波浪潮 —— 这浪潮,要帮无数像他这样的年轻人,靠 “一技之长” 活出不一样的日子。
其实早在几十年前,就有人琢磨着办 “学手艺” 的学校了。鸦片战争后,曾国藩、李鸿章搞洋务运动,办工厂、造枪炮,可找来找去,没几个会摆弄机器的人。江南制造局刚办的时候,造枪炮的师傅都是从外国聘来的,工资高得吓人,还动不动就摆架子。李鸿章看着着急,跟曾国藩商量:“总不能一直靠外国人,得自己培养人,办个学堂,教年轻人学技术,以后工厂才能自己撑起来。”
于是在 1867 年,江南制造局就办了 “工艺学堂”,教天文、算学,还有机器制造的基础。可那时候的人,大多觉得 “读书做官” 才是正途,学手艺是 “下等人干的事”,学堂招了大半年,才招到几十个学生。而且课程太偏理论,学生学了半天,还是不会修机器、造零件,毕业出去也没人敢用。这学堂办了没几年,就不了了之了。
可到了陈阿福去的 1905 年,情况不一样了。这时候清朝已经搞 “新政”,鼓励办实业,工厂越开越多,纺织厂、机械厂、矿场,到处都缺会手艺的人。江南制造局的技工学校,吸取了以前的教训,不搞虚的,上来就教实操。陈阿福学的是铁匠,每天天不亮就起来,先跟着师傅练抡铁锤 —— 一开始锤柄都握不稳,练了半个月,胳膊肿得像馒头,才慢慢能把铁块砸得有模有样。
学堂的课程也实在,上午学两个时辰的算术、机械原理,下午就泡在工场里。师傅都是厂里干了十几年的老技工,不怎么会讲大道理,但手上的活没话说。有次陈阿福学打齿轮,铁块烧得太硬,一锤下去崩了个豁口,他急得快哭了。师傅没骂他,只是拿起另一块铁,一边烧一边说:“火要烧到橘红色,不能太旺也不能太弱,锤要砸在中心,力道得匀。” 说着就抡起锤,几下就打出个规整的齿轮。陈阿福看着师傅手上的老茧,突然明白:手艺这东西,不是靠说的,是靠练的。
在学堂里,陈阿福第一次吃上了饱饭 —— 每天两顿干饭,中午还有一碗菜汤,偶尔能见到点肉。他把省下的钱寄回乡下,给家里写信说:“我在上海学手艺,以后能当技工,不用再扛包了。” 家里回信说,乡亲们都羡慕,说他 “走了正路”。其实不光是他,学堂里的其他学生,大多是像他这样的穷小子,有的是农民,有的是小商贩,还有的是学徒,大家都憋着一股劲:学好手艺,以后能挺直腰杆过日子。
这时候,全国各地的技工学校也多了起来。天津的北洋工艺学堂,教纺织、染色;湖北的汉阳铁厂学堂,教采矿、冶金;广州的机器局学堂,教船舶修理。这些学堂有个共同点:不搞 “学而优则仕”,只教 “学以致用”。比如北洋工艺学堂的纺织科,学生要在厂里实习半年,从纺纱到织布,每一道工序都得会;汉阳铁厂学堂的学生,要下到矿井里,学看矿脉、用采矿机,手上、脸上经常沾得黑乎乎的,但没人抱怨 —— 大家都知道,这些 “苦”,是以后吃饭的本钱。
可还是有人不理解。有次陈阿福回家,村里的老秀才见了他,摇着头说:“好好的人,不去读书考功名,跑去学打铁,真是可惜了。” 陈阿福没反驳,只是把自己打的一把镰刀送给老秀才 —— 这镰刀又锋利又耐用,老秀才用了半年,再也没说过闲话。其实那时候的社会,对 “技工” 的看法正在慢慢变:以前觉得技工 “低人一等”,可眼看着工厂里的技工一个月能拿两三块银元,比乡下的秀才挣得还多,不少人开始琢磨:学手艺,好像也不是件丢人的事。
到了民国初年,职业教育更是火了起来。这时候出了个叫黄炎培的人,他本来是教书的,看到很多年轻人毕业就失业,要么只会背书,要么啥手艺没有,心里着急。他说:“教育要是不能让年轻人有饭吃,那就是白办。职业教育,就是要让无业者有业,有业者乐业。”
1917 年,黄炎培在上海办了 “中华职业学校”,这学校跟以前的技工学校不一样,不光教工业手艺,还教商业、农业 —— 有木工科、铁工科、纺织科,还有商科、农科。学校门口挂着一副对联:“双手万能,手脑并用”,意思就是既要会想,也要会干。
中华职业学校的学生,早上要做 “晨操”,不是普通的做操,是练木工、铁工的基本功,比如刨木头、拧螺丝;上课的时候,老师会带学生去工厂参观,让他们看机器怎么转,布料怎么织;毕业的时候,学校还会帮学生找工作 —— 纺织科的学生,大多能进上海的永安纱厂、申新纱厂;铁工科的学生,能进造船厂、机械厂。
有个叫李梅的女生,家里是开小杂货铺的,父母本来想让她嫁人,她却偷偷报考了中华职业学校的纺织科。一开始家里反对,说 “女孩子学织布,像什么样子”,可李梅坚持要去。在学校里,她学得特别认真,别人练织布机练一个时辰,她练两个时辰,手上磨出了茧子也不在乎。毕业的时候,她因为技术好,被永安纱厂聘为技术员,一个月能拿四块银元,比她父亲开杂货铺挣得还多。她父母后来逢人就说:“没想到学手艺,女孩子也能有出息。”
那时候的职业学校,还有个特点:不看身份,谁都能来。不管是农民的孩子,还是商人的孩子,只要愿意学,都能报名。有个叫王大山的学生,以前是给人拉黄包车的,听说中华职业学校招生,就凑钱报了名。他白天上课,晚上还去拉车挣钱,虽然累,但学得特别刻苦。毕业的时候,他进了上海造船厂,学修船的发动机,没几年就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,还带了几个徒弟。他常跟徒弟说:“我以前拉车,不知道明天能不能有活干;现在学了手艺,心里踏实,这就是职业教育的好。”
到了抗战时期,职业教育又有了新的用处。那时候很多工厂从沿海迁到内地,急需技术工人造枪炮、修机器。重庆、昆明、西安这些地方,办起了不少 “战时技工学校”,专门培养军工、机械、电讯人才。这些学校条件很苦,没有像样的工场,就用简陋的工具代替;没有足够的教材,老师就自己编;学生们住在茅草屋里,冬天冷得睡不着,夏天蚊子咬得满腿包,但没人叫苦 —— 大家都知道,自己学的手艺,能帮着打鬼子,能保家卫国。
昆明有个 “兵工技工学校”,学生们学的是造手榴弹、修步枪。有次厂里的机器坏了,外国工程师修了两天没修好,几个学生跟着师傅一起琢磨,用自己学的知识,居然把机器修好了。外国工程师惊讶地说:“没想到中国的年轻技工这么厉害!” 学生们听了,心里都特别骄傲 —— 他们知道,自己的手艺,不光能吃饭,还能为国家出力。
抗战胜利后,职业教育继续发展。南京、北平、广州这些大城市,都办了专门的职业学校,有的叫 “高级技工学校”,有的叫 “工业职业学校”。课程也更细了,有教汽车修理的,有教无线电的,还有教会计、秘书的 —— 不光是工业,商业、服务业也开始需要有专业技能的人。
新中国成立后,职业教育更是迎来了大发展。那时候国家要搞工业化,建工厂、修铁路、造汽车,急需大量技术工人。政府在全国各地办了几百所技工学校,比如长春的 “第一汽车制造厂技工学校”,专门为一汽培养汽车工人;沈阳的 “机床厂技工学校”,培养机床操作工人。这些学校的学生,毕业后大多能进国营工厂,成为 “正式工人”,有稳定的工资,还有福利,在当时是很让人羡慕的。
就像当年的陈阿福,他在江南制造局技工学校毕业后,成了厂里的铁匠,后来又学了机器修理,慢慢成了技术骨干。他的儿子,也进了技工学校,学的是汽车修理,后来在上海的汽车厂工作。陈阿福老了的时候,看着儿子手上的工具,笑着说:“我那时候学手艺,是为了不饿肚子;现在你们学手艺,是为了造更好的东西,这就是进步啊。”
其实这么多年来,职业教育的核心一直没变 —— 帮年轻人学 “一技之长”,让他们有能力养活自己,有能力为社会做事。从清末的技工学校,到民国的职业学校,再到现在的职业技术学院,不管名字怎么变,不管教的手艺怎么更新,这个核心一直都在。
以前有人觉得,职业教育是 “次等教育”,只有成绩不好的人才去学。可实际上,职业教育救了很多人的命,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。就像陈阿福,要是没去技工学校,可能一辈子都在码头扛包;像李梅,要是没学纺织,可能早就嫁人生子,一辈子围着灶台转;像抗战时期的那些学生,要是没学军工技术,可能就没法为国家出力。他们用自己的经历证明:手艺不是 “下等” 的,靠手艺吃饭,靠手艺做事,一样能活得有尊严,一样能有出息。
现在的职业教育,教的手艺更先进了,有教机器人操作的,有教无人机驾驶的,有教新能源汽车修理的,还有教电子商务、幼儿保育的。但不管教什么,本质上还是当年黄炎培说的 “双手万能,手脑并用”—— 既要会想,也要会干;既要学技术,也要学做人。
回头看一百多年前的那些技工学校,条件简陋,设备短缺,甚至连教材都不全。可就是这些不起眼的学校,像种子一样,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,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技术工人。他们造机器、织布料、修汽车、建铁路,用自己的手艺,撑起了中国的工业发展,撑起了无数家庭的希望。
就像 1905 年上海的那个夏天,陈阿福攥着干馒头,走进江南制造局的大门时,他不会想到,自己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,还成了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的一个小小缩影。这个缩影告诉我们:教育不只是为了考大学、当白领,更是为了让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,都能靠自己的双手,活出不一样的人生。
职业教育的故事,还在继续。现在还有很多像陈阿福、李梅这样的年轻人,走进职业学校,学习手艺,为自己的未来打拼。他们的故事,和一百多年前的那些故事一样,都在证明:一技之长,能安身立命;职业教育,能点亮人生。这,就是职业教育最朴素也最珍贵的意义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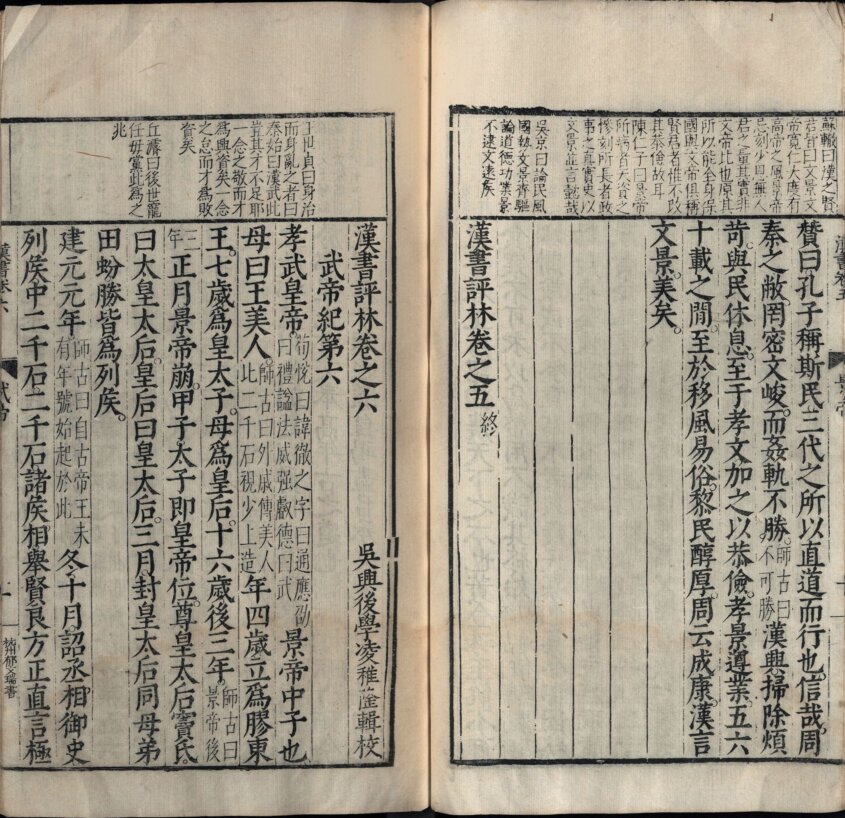





近代职业教育发展:办技工学校帮年轻人学“一技之长”:等您坐沙发呢!